卡尔·杰拉西认为,他可能是目前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冬季班任教的年龄最大的教授。但是,尽管他作为有机化学家的职业生涯漫长而可敬,但他最著名的是与口服避孕药但他也从事皮质类固醇、天然产品和物理方法方面的研究——他现在在一个关于科学和戏剧的跨学科研讨会上教书。本·瓦尔斯勒向他讲述了他的艺术生活。
你曾是一名杰出的化学家,是什么促使你转向写小说?
我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实际上是我的思想生活,在一个出人意料的晚期:在我60多岁或60多岁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一种知识走私者的生活,会很有趣。
正是我处理药丸和避孕药具的工作让我意识到,如果一个人谈论科学发现的社会后果,他必须与非常广泛的公众交流,并且以一种与科学家习惯的非常不同的方式。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么对你所说的不感兴趣,要么害怕,要么声称他们听不懂,即使你试图解释,他们也不听。
因此,我想我要走私。我将把它隐藏在我最初所说的“科幻小说”中,以完全区别于科幻小说。换句话说,我在伪或准虚构语境中所描述的一切,实际上要么是真实的,要么是可信的。我没有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我没有永动机和类似的东西,这些在科幻小说中可能非常有趣,但对我的目的并不适用。
我写了五部小说,其中四部是科幻类的,因此,应该是有趣的,令人兴奋的,希望写得好,人们喜欢读。但当他们完成时,他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一些东西。
我这样做了15年,那时我已经70多岁了。那时,我正往返于旧金山和伦敦之间。当然,伦敦是戏剧之城。我去剧院看了几十年了,每年大概看30部戏,所以我看了几百部戏。我主要看智力剧。我说的是汤姆·斯托帕德或艾伦·贝内特——我不太去看音乐剧或捧腹大笑的喜剧。
我认为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想写点什么,他也必须接触到它。所以,如果你不读小说,你就不能成为一个自学成才的小说家。如果你不去剧院,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自学成才的剧作家。
那时候我还没打算写剧本,我还记得1996年在皇家国家剧院的科特斯洛剧院看斯蒂芬·波利科夫的作品被太阳弄瞎了眼睛。一部人们已经不太记得的戏剧,但那是一部非常纯粹的化学戏剧,而且很少有化学戏剧,它涉及冷聚变的争论。
你必须是一个愿意在公共场合洗脏实验室大褂的内部人士
那时,我还不知道波利科夫是物理化学家的兄弟Martyn Poliakoff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很好地展示了科学家的特殊行为。我记得我走出剧院,告诉我妻子,‘我现在要写一个剧本’。不是因为波利科夫,而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特别谈到了机械繁殖时代的性,性与繁殖的分离——我说,‘我要写一部关于它的戏剧’。
那出戏结果是一个完美的误解它于1998年在爱丁堡边缘剧院开幕,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英国广播公司对它进行了重点报道爱丁堡的夜晚以及BBC世界广播。现在,它已被翻译成12种语言,并在许多地方演出。
我被迷住了。我着迷于以下原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科学家,从17th世纪以来,你几乎可以说从伽利略或培根开始,我们就不能再以对话的形式写作了。从希腊到十七世纪th世纪以来,人们写了很多对话形式。我指的不是戏剧,而是对话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唯一遗留下来的就是戏剧写作。
我的前几部戏剧都是关于科学的,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误解第二个问题氧气,这是我和一位著名的化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一起写的罗尔德·霍夫曼来自康奈尔[美国大学]。
第三个叫做微积分它讲述了牛顿和莱布尼茨之间关于谁发明微积分的丑闻。坦白地说,我提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问题。也许这么说有点不礼貌,但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可以是一坨屎吗?牛顿的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其他人也是如此,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真的认为这是我最好的戏剧之一,因为我对英国最有权势的科学家、造币厂的主人、皇家学会的主席牛顿痴迷于竞争的著名冲突做了大量的研究。无论是胡克,还是弗兰斯蒂德,尤其是莱布尼茨;在每一种情况下,他都想成为第一个。他任命了一个由11名皇家学会成员组成的匿名委员会,由他们来评判谁是第一名。很少有人知道,但也有据可查的是,他后来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那个委员会。
我的小说和戏剧更多地关注科学家的行为和文化方面。换句话说,我们是如何表现的,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因为我们所做的,当然,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科学记者,他们描述了我们是如何做科学的。但要描述我们的行为,你必须是内部人士。而且你必须是一个愿意在公共场合洗脏实验室大褂的内部人员。这也是我自己的实验服,所以我不是一个谈论“他们化学家”的揭发丑闻的记者。不,我写的是我们自己。这是一个集体我的过失部分地,但不是全部我的过失因为很多特殊的方面也是非常积极的。
我们是一门可能是所有学科中最具学院性的学科。同时,竞争最残酷,而这种结合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另一个是野心。没有问题。我们想成为第一。我们有一个奥运会,你可能会说,只有金牌,没有银牌或铜牌。
这种雄心既是许多科学家每周工作七八十小时的养料,同时也是毒药。这就是营养与毒药之间的平衡——这是一个非常棘手、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我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可能没有成功,但我试图在我的戏剧和小说中展示和描述。
你认为科学家的职业训练你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工作和思考吗?这对你写小说和剧本的方式有影响吗?
我认为不是,除了在一种情况下。我们是科学家,因为我们好奇。这总是人们投身科学的首要动机。
我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好奇的人。这种好奇心确实反映在我写的戏剧类型和我所好奇的东西上。我会说我想出了新东西。毫无疑问我的微积分关于牛顿和莱布尼茨的戏剧包含了非常有趣的新材料。
但说到风格,答案绝对是否定的。因为作为科学家,我们写作纯粹是为了传递信息,我们应该做到精确。真正重要的是内容,其次才是风格。你可以用很差的风格写一篇非常好的科学论文,如果科学是伟大的,它仍然会被认为是一篇伟大的论文。如果文章风格很好,但科学水平一般,那就是一篇平庸的论文。
但在文学写作中却不是这样,在广泛的语境中风格是非常不同的。你必须隐藏信息传输。即使你对它感兴趣,也要隐藏起来。它不需要很清楚,否则人们会称之为说教,而说教是任何书评中最具侮辱性的术语。我完全意识到其中的危险,甚至承认自己有说教的动机也是危险的。但你知道,我已经足够大了,可以这样做,并说,'好吧,管它呢!”
当你在写科幻小说时,你的目的是交流关于某个科学主题的信息,在雷达下偷偷摸摸地把它带进来。大多数小说作者都没有这样的意图。你会根据其他作者的不同参数来判断一本书或戏剧的成功吗?
完全。从定义上讲,我不写畅销书,但我写长篇畅销书。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的科幻四部曲的第一卷,康托尔的困境,现在是第28或29次印刷。现在每年还在重印。
它在学院和大学中被部分用作推荐读物。但它特别告诉年轻的科学家——我说的年轻是指20多岁的人——投身科学是什么样子的。它涉及大学、研究生、博士后和教授;行为不当和吸引人的行为。我是在1990年写的,现在仍然是最新的,非常有意义。
小说中的对话让我们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探索那些道德上的“灰色”领域。你想不想看到更多的尝试被投入到民粹主义戏剧中,比如肥皂剧,来尝试和处理这些伦理问题?
我们不都是奇爱或弗兰肯斯坦,白痴学者或书呆子
我会让你失望,拒绝你因为我不是肥皂剧迷。我不喜欢把它降低到一个更低的水平。我不喜欢看到它们被过分简化。所以,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但还有另一个问题。我告诉你的一切听起来都很美好,但事实上,整个剧院都对涉及戏剧(科学内容)的事情持怀疑态度。
有一些巨大的成功。哥本哈根迈克尔·弗莱恩的作品就是一个例子。被太阳弄瞎了眼睛例如,由波利科夫创作的,是一部非常好的戏剧,但并不是非常成功。我不认为它会转移到科特斯洛之外。
有些戏剧可以被称为科学剧,比如汤姆·斯托帕德的戏剧世外桃源。这不是一部纯粹的科学剧,但它包含了科学:它涉及费马大定理。里面有一些混沌理论的概念。
我认为剧院——我发现大多数地方都是这样——是可疑的。他们觉得我们科学家……正在接管世界,现在,我们想进入剧院,把它也带到那里。毫无疑问,很少有戏剧能登上大舞台。
我的很多讲座,比如我下周要讲的一个叫做“科学能为剧院做什么”和“剧院能为科学做什么”。“嗯,我当然对第二个感兴趣。不是科学本身,而是科学家。我真的很想告诉大家,我们也许不是“正常人”,但却是有趣的人。我们并不都是奇爱或科学怪人,也不都是白痴学者或书呆子,但我们也覆盖了行为的高斯分布曲线,其中的中间部分是大多数人不熟悉的,但可能会觉得相当有趣的。
阅读更多关于科学与艺术在我们的主题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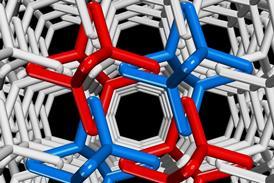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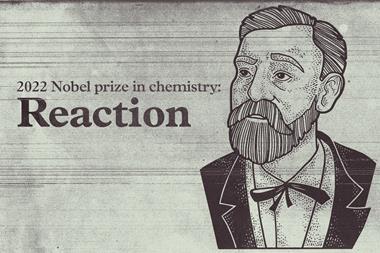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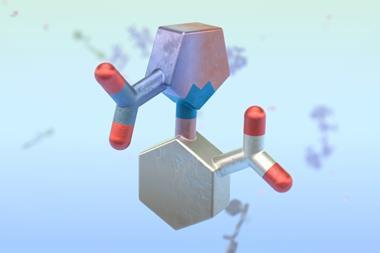






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