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 Peplow说,与一个受到谴责的国家断绝学术联系弊大于利

这是一个阴冷的夏天。似乎每周都有新的暴行在上演:流血的儿童尸体被抬过加沙的街道;被击落的MH17客机残骸散落在乌克兰东部的向日葵田里;叙利亚酷刑和处决持不同政见者的可怕照片。
这些地区冲突造成的令人心碎的伤亡不容忽视,但作为个人,我们实际上无力减轻这种痛苦。一些科学家认为,他们手中为数不多的影响政治变革的工具之一是学术抵制——停止与在目标国家工作的科学家的所有接触。
自从以色列最近在加沙地带采取军事行动以来,抵制以色列学术机构的呼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但是,这种抵制会限制思想的自由交流,从而破坏科学的基本原则吗?我们如何确定它们是否有效?
实践,而不是原则
尽管一些美国学术团体支持对以色列的学术抵制,但大多数领先的科学机构坚决反对这一想法,理由是它们以歧视性的方式限制言论自由。例如,英国皇家学会表示,“因为国籍、种族、性别、语言、宗教或政治信仰等问题而对科学家或其他学者进行全面抵制是不可接受的”。
尽管坚持绝对原则很诱人,但也必须有例外——例如,我们会激烈地捍卫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大学里与希特勒的合作者进行学术交流吗?
其他反对抵制的人认为科学应该远离政治,但这充其量是naïve——科学与社会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事实上,许多科学组织都热衷于利用科学合作来改善国际关系。
我们不应该把评估建立在原则上,而是应该考虑抵制可能带来的好处是否超过它可能造成的伤害。目前还远不清楚种族隔离时代是否存在抵制南非学者以任何方式促成了他们政府的崩溃。一些人认为这确实增加了变革的压力;另一些人则声称,它没有任何影响,甚至对大学部门造成了长期损害。相比之下,更确定的是,抵制针对的是学者,伤害的正是那些可能在促进本国政治变革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人。
影响评估
那么,什么时候学术抵制才是真正值得的呢?2003年,牛津大学的四位科学家提出了争论1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并且在学术界几乎得到普遍支持时,才应该考虑抵制。此外,它不应该只是象征性的抗议——应该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它将迫使一个政权改变其不良行为,它应该与更广泛的国际制裁携手并进。
根据这些标准,有人可能会说,目前对俄罗斯的学术抵制比对以色列更有理由。美国政府显然是这么认为的。今年3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这一事件可能被合理地称为异常)后不久,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能源部等机构工作的科学家们被命令这样做停止了与俄罗斯同事的合作.
与经济制裁相比,学术抵制在迫使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撤回对乌克兰分裂分子的支持方面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但其影响不容忽视。普京近年来在科学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如果俄罗斯不断增长的国际合作项目被削减,俄罗斯将会损失惨重。
例如,俄罗斯和英国去年签署了一项协议,扩大在粒子物理、能源效率和空间科学等领域的合作。英国商务大臣文斯·凯布尔(Vince Cable)强调,他希望利用这些协议来推动英国高等教育成为“出口产业”。如果科学可以被用作促进和奖励良好国际关系的政治工具,那么暂停这些协议可能会对那些违反国际法的政府起到抑制作用。
但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标准需要考虑:抵制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吗?切断与俄罗斯学术界的所有联系可能会扼杀知识自由,而这最终可能有助于创造一个更温和的政治气候。总的来说,与学术抵制可能实际施加的政治压力相比,这种风险太大了。
如果目标是引起全世界对渎职行为的关注,那么有力和反复的谴责所达到的结果与学术抵制大致相同。与此同时,国际合作可以为推动专制政权变革的科学家提供支持;像这样的项目芝麻(同步加速器在中东的实验应用),甚至可以联合来自彼此不和的国家的研究人员。科学不应置身于政治之外,但它应始终评估其干预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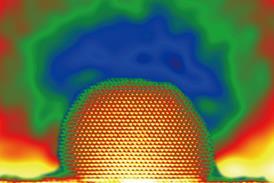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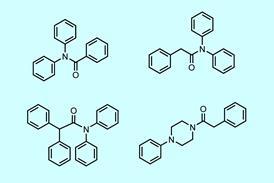








暂无评论